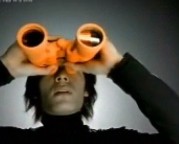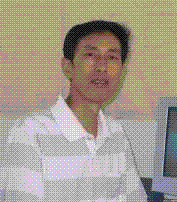本报记者 李望/文 洪骋/图
他当过宾馆服务员、村支书、乡镇干部,最后当上了省报记者,但在他的生命中只有一个愿望,也就是当个出色的记者,这正如他在自己曾工作过的一份报纸内部资料上所写的那样:"做记者,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愿望,我苦苦摸索了8年……"他的夙愿终成现实,但记者之路才刚刚开始不过4年,正在如火如荼的事业颠峰时刻,病魔却和他不期而遇……
他就是被媒体称为"新闻硬汉"的《三秦都市报》优秀记者张军利。2004年8月,老张被诊断为重症肌无力合并胸腺瘤,仅仅3个多月,严重的病痛已使张军利的体重已由病前的170多斤减到了不足120斤,而与此同时花费的医疗费用多达10万元之巨。
这个巨额的看病支出如今成了张军利夫妇和他们家人头痛的问题。如何让大多数不同老百姓能看得起病这个沉重而复杂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
"新闻硬汉"病述从业经历
12月初的一天,记者第二次走进了唐都医院神经理疗中心看望这位昔日的同事。那天的天气格外暖和,当记者走进中心的林荫道上时,远远就看到边读报边晒太阳的老张夫妇,老张坐在椅子上,妻子坐旁边的小凳子上,夫妇俩还不时的相互指着报纸说些什么。在他们身旁是清洁的小道、葱绿的松柏和草坪,一切显得柔和而恬静。
老张看到了记者马上放下了手中的报纸站了起来并招手示意,他的妻子也站了起来,老张依然像以前在单位那样直爽、热情,虽然他目前在病中。
"老张,你瘦多了……"记者惋惜的对老张说。
"是……啊……!",他点着头,伸出了5个白皙的手指。记者想不到仅仅4个月的时间,这个170多斤的"张胖子"已被病魔削去了50多斤,身体变得白皙而瘦消,但他的眉毛依然又黑又浓。
比起半个月前,老张的脸色红润多了,他可以说话了,可以再不用笔书与记者交流,但他的鼻孔依然插着鼻饲导管,脖子上依然缠了厚厚的一层白沙带。在和记者交谈中,他说得很慢,很吃力,他尽量的说清楚每一个字,尽量避免导管对发音的影响,但仍显得力不从心。大约10几分钟的时间,老张的额头就渗满了汗珠。
老张说,从事新闻工作,是他大学毕业后选择职业的唯一愿望,然而阴差阳错,他未能进入新闻单位的大门,一差就是8年多,8年来,他做过宾馆服务员、村支部书记、乡镇干部,他迷茫过、苦恼过,他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1995年8月,陕西日报社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给了老张圆梦的机会,老张从此把新闻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8年的时间里,老张一边干着自己的老本行,一边刻苦的学习新闻采写知识,他自费订阅了《新闻知识》、《新闻与写作》等各种书籍刊物,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实践,8年的时间里,老张每年在县、市甚至省级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多达上百篇。2002年年初,又一次偶然的机会,经朋友推荐,老张进入了当时的《今早报》,8年的新闻梦终究变为现实。老张说,他在内部刊物《早报编采》写过一篇名为《从乡镇干部到省报记者》的文章,"8年的苦苦摸索终成现实,我感慨万千!"
从乡下走进大都市后的老张人地两生、业务生疏,为了熟悉西安,他买了一张西安市区图,每采访过一个地方就在地图上画个圈,长此以往,那张地图被划的密密麻麻,西安的地名也就满满的装在了他的心里。为了赶上业务,他每天走出报社都带上3个以上的新闻线索,保证每天都有文章见报。两个月过去了,老张的勤劳和敬业终于有了成绩,他获得了月奖中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并得到了报社老总的肯定和同事们的认可。
新闻硬汉不图虚名
翻开老张2001年1月31日--2004年6月26日三大本剪报本(其中2003年3月28日--2003年10月29日的剪报本因其它原因记者没有见到。)沉甸甸的,每一页剪报,每一篇报道都可以感受到老张作为一名记者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
《华商报》称他"新闻硬汉",《三秦都市报》的同事们称他"张执著",这些崇高的称谓,在他3年多的剪贴的稿件中可窥见一斑。
在老张的剪报本上有一组2001年3月份《今早报》刊发的《"母子情"有常识性错误》的连续报道。这是一位读者对当时正在建设中的西安浐河公园仿真雕像中"母子情"的雕像提出疑问。"正常人趴在地上双膝着地小腿抬起,脚应与躯干平行?还是与躯干垂直?"(那尊雕像中小孩的脚是与其躯干垂直的。)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线索,当时在热线本上已经躺了三天,结果被老张拉出来后,连续作了8篇报道,最终引起了西安市规划局关注城市"艺术垃圾",展开一场消除城市"艺术垃圾"的风潮。有同事戏称这是老张入行以来的第一桶"金"。
打开老张那厚厚的每套剪报本,连续报道不计其数,批评稿件比比皆是,这种惩恶扬善、肝胆正义、刨根寻底的精神成了老张以后笔耕不辍的源泉,也正是有了这样追寻真理的精神,老张的业务能力如日中天,他在不断的挑战每一个新的高度,由写小消息逐渐涉及做大篇幅的深度报道。
在他的第三本剪报本上(三秦都市报工作以后),大篇幅的报道占了绝大多数纸页,里面有除恶扬善的曝光稿件也有催人泪下的人文稿件。《16岁的妈妈你在哪里?》、《陕西娃单飞越楚河汉界》、《坠楼案发生在刑警队》、《洛川县卫生局丢牌子内幕》、《西安火车站周边环境调查》、《抗洪前线的12张脸》等数十篇深度报道,人们通过他细腻而深刻的文章去思考每一件新闻事实。
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和自身不凡的经历(乡镇工作经历),2004年3月,单位提名让他参与了反映三农问题,最终轰动全国的《五曲湾纪事》大型采访。
重病突起7月天
不幸的是,病魔就在这位新闻硬汉的事业如火如荼之时和他不期而遇,和老张同租单元房的一位同事向记者介绍了他发病的前前后后。
"7月份他参与报道的《靖边豪赌调查》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凡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军利就开始脖子疼,大家都说是落枕,医生检查后也说没有大碍。后来,他慢慢地觉得吞咽困难,不想吃饭,连左胳膊都有些发酸,抬不起来。都以为是脖子疼引起的,连他自己也没有在意。直到9月1日凌晨3点多那次差点要了命的窒息,我才感觉他病情的严重性。那天晚上我们一起从报社回家。边走边停地上到我们租住的六楼时,军利早已上气不接下气。看到他实在太累,那晚我们没有多聊,让他早点休息。谁料,凌晨三点多,他几乎是破门而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只见他面红耳赤,两只手疯狂地在胸前乱舞着,我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便着急地帮助他进行呼吸。几分钟后,他终于缓过气来,那时我早已满头大汗。"
"第二天一大早,军利还要去报社忙手头的一个采访,我硬是把他扯进了红会医院。经过大半天的检查,医院认为所有的症状几乎都不可能是颈椎疼痛引起的,于是入住耳鼻喉科进一步接受检查。入院第三天,军利的两只胳膊突然都抬不起来了,他哭了,眼泪不多,但是说很伤心,伤心自己所钟爱的新闻事业干得正起劲,突然却病倒了。看得出他似乎也有某种预感。那天我也哭了,只是没敢当他的面。因为,大夫已经告诉我这绝不是一般的头疼脑热。随后又转入西京医院,老张被查出患上了'重症肌无力合并胸腺瘤',后又转入西安唐都医院神经专科接受治疗。"这位同事回忆起与老张共事的日日夜夜,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老张的主治大夫郭永洲向记者介绍,"重症肌无力"是神经-肌肉接头疾病的典型代表,它是神经-肌肉接头处传递功能障碍疾病,老张的病情就是这种传递功能免疫力下降,直到目前,这种病害不能确定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它的临床表现就是部分或全身骨骼肌肉易于疲劳,常具有活动后加重、休息后减轻,上午时轻微下午时严重。而这种病的患者中胸腺肌几乎都有异常,10%--15%的患者都伴随有胸腺瘤,约70%的患者有胸腺肥大。
妻子眼中的老张
在老张的床头摞着一沓报纸,"他自从可以下床后,每天都要看报纸和电视,我真那他没办法!"妻子秦晓霞笑着对记者说,但说起了丈夫,她哽咽住了。
老张的老家在渭北澄城县,据西安不到150千米,有高速公路和平坦的108国道,来回驱车不到三个小时,但秦晓霞说:"老张除了每年的两个黄金周和春节外,所有的时间都忙在了工作上,平时都是她在礼拜天带孩子来西安,他病了,我可以好好陪陪他了……",秦晓霞并没有显露出委屈,反而对丈夫表现出了无法用语言表现出的敬意。
记者说"靖边豪赌案"有人用10万重金要老张不要在发追踪报道的事情时,秦晓霞显得很激动。她说:"当时军利给我说过,那几天给他送钱的电话不下十个,但他根本不为所动,他很正直,当记者也是这个原因,他要做的事情10头牛也拉不回来!"。
看病的钱从哪里来?
在电脑数据中,张军利从9月14日入院治疗至12月12日截至总共花费89391.67元,这些日子里(87天)平均每天的医疗费用多达1027元。现在每天在医院的各种费用仍不少于100元。主治医师郭永洲说,张军利目前仍在康复期,要完全康复还需要一段时间,而这种病在康复后的半年内还有复发的可能性。
记者问张的妻子秦晓霞如此巨额的医疗费用,一个工薪家庭如何承受的起,秦晓霞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她不愿意向记者说明,这也许是因为张军利,这位34岁的"新闻硬汉"从不愿意在同事面前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
秦晓霞只说"老张军利每月2000多块钱左右,从8月末病发至今,各种花费已经超过了10万元……"。秦晓霞说,军利入院后,他的工作单位捐过1万多元加上其它单位和个人总共近3万元。
记者的老家和张军利同是渭北高原的乡村,张军利当年在这个地区作乡镇干部,按照这个地区基层行政干部的收入,他每月的薪金一般在千元左右,大多数地方可能还超不过千元,而他的妻子秦晓霞是当地的乡村教师,按照记者了解的情况,其月收入至多也仅800元左右(秦晓霞在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点),有些地方的教师工资还不能保证及时发放,虽然如此,张军利夫妇的收入在渭北高原的普通百姓眼中"还是不错的",因为在这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众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一年的经济纯收入不足2000元。
张军利来西安从事媒体行业,这是他的理想,但从两者收入差距来看,这也是他"半路改行"的另一个原因。所以他不仅仅是为了理想,更是为了生活而远离妻儿投身媒体。也许从病魔降临的那天起,张军利顾虑了。
相关连接:
"新闻硬汉"的悲哀
据《华商报》对"陕西记者生存现状"进行了专题调查显示:
■平均47.3%的记者没有基本社会保险
■75.4%的记者曾在采访中遭遇过辱骂、诋毁
■80.1%的记者认为最大价值在于得到公众的认可,为政府分忧、为民众解难
新闻记者流动性较强,有42.7%的人曾在两家以上媒体工作过;74.4%的记者从事新闻工作3年以上,10年以上者占到26.6%。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5.5%的家庭里有2人以上在新闻媒体工作;另外,40.1%没有相应的新闻专业技术职称,20.8%的记者不是陕西人。
事业至上愧对家庭
"加班、熬夜、四处奔波"是记者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太忙了",记者很难像正常人那样恋爱、结婚、生儿育女。76.4%的记者在25岁以后结婚,近两成人在30岁以后生育;认为从事新闻工作对婚恋"影响很大"和"有些影响"的分别占18.1%、47%。
记者职业的特殊性也影响到其家庭生活。近三成人没时间陪伴家人,30.2%的人一周只有2-4个小时与家人在一起。由于回家总是太晚,36.2%的家人经常抱怨,49.9%的家人偶尔唠叨。不过,"打是亲,骂是爱",抱怨虽然难免,家人对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支持率却颇高,非常支持与支持所占比例达91.1%,令人欣慰。
近七成人月收入低于1500元
众所周知,记者所从事的是高风险、高强度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的劳动,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记者的收入应该相对较高。但调查显示,68.8%的人每月收入低于1500元,91%的人月收入在2500元以下,31.8%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这与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相比,收入偏低。正因为此,51.3%的记者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
半数以上记者亚健康或不健康
记者群里普遍存在着透支健康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以中青年为主的记者人群中,有58%的人处于亚健康或患病状态,在患病人群中,有2-3种疾病的人占到35.8%。记者目前最严重的疾病依次为:肠胃病(30.4%)、颈椎病(19.8%)、眼科疾病(13.5%)、头痛等神经痛(11.9%)、便秘(5.3%)、心脑血管病(3.9%)等。
九成以上记者每天平均睡眠不足8小时
记者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与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生活不规律、锻炼时间少、未定期体检等因素有关。调查表明,36.9%的记者觉得工作压力非常大;56.3%的记者认为压力有些大,但可以承受;感到没什么压力者仅占6.9%。压力的来源主要包括竞争太激烈、经济收入低、工作没有稳定感等,分别占47%、23.2%、20.9%。
同时,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记者占38.2%,8小时以上的占到87.5%;九成多的人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85.3%的人经常或有时失眠,72.7%的人寝食不规律。另外,74.3%的人平均一周用来锻炼的时间不足2小时;只有25.4%的人定期体检。
近一半记者无基本社会保险
帮民工讨工钱,救助失学的孩子,关爱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记者时常为社会弱势群体奔走。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基本社会保险都没有。
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有47.3%的记者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74.7%的人没有意外伤害保险。对于"单位是否与您签订了正规的劳动合同"这个问题,45.5%的人回答"否"。令人忧虑的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记者基本社会保险的缺失,若任此局面发展下去,恐怕越来越多的记者会沦为"新闻民工"。记者的工作、学习条件也一般。73.2%的人靠骑车、乘公交车、出租车外出采访;50.8%的人没有接受培训的机会。
舆论监督常遭"黑手"
伸张正义、揭黑斗恶,为政府分忧、为百姓鼓与呼,在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中,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维护与保障记者自身合法权益也迫在眉睫。
调查结果显示,75.4%的记者在采访中曾遭辱骂、诋毁,42.2%的人因舆论监督报道遭遇过打击、报复。同时,暴力、恶意诉讼、地方保护、黑势力、官僚主义也在侵蚀着记者的权益和安全。"只有记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94.4%的人认为"非常需要"专门的法律法规来保护记者合法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91.6%认为国家应尽快制订《新闻法》。
忍辱负重无怨无悔
尽管记者的职业之旅充满艰难险阻,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在理想的支配下勇敢地跨入记者行列,对"您选择记者职业是出于哪种考虑"这个问题,68.1%的人回答是"个人理想",9%的人选择了"收入高"和"社会地位高"。同时,76%的人认为记者是"肩负一定社会责任的特殊群体";63.7%的人表示,神圣的使命感、强烈的责任心和人生追求是自己坚守记者岗位的动力和原因;80.1%的人认为记者的最大价值在于"得到公众的认可"、"为政府分忧、为民众解难"。


 重症肌无力病友之家 → 问答讨论 → 医院费用大展览,看了不跟贴我要和你急!
重症肌无力病友之家 → 问答讨论 → 医院费用大展览,看了不跟贴我要和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