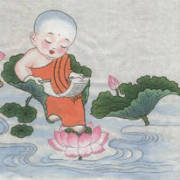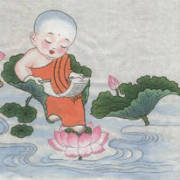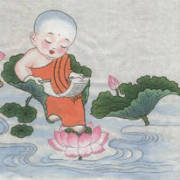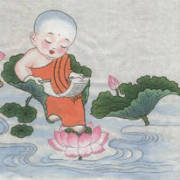生死谈
文/清昭
“死亡是什么?生命又是什么?”儿时,我曾相当多地想到过生与死的问题。也许少年忧郁,在每一个还不足够成熟,略带青涩的成长年代,这或许是所有少年有过的困惑与共鸣。
时钟总是越走越快。快得还来不及品味,最美的时间就已擦肩而过,将人用力一抛,便浸淫进现实中,让人无法自拔。也许,正像某些人的观点,生与死从来是医生、哲学家,和孩子们才会想的问题。医生眼中的生死直观而冰冷;哲学家眼中的生死抽象而复杂。也许,只有孩子们眼中的生与死才是灵动而真实的。既令人畏惧恐怖,又带着美丽与几分可爱。因为孩子们的眼中,生死是浪漫的。老人们常会对那时的我们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死了,我们的灵魂还在,我们会去一个非常快乐,能带来无比幸福的大花园,那里叫天堂。”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寻找通往天堂的路。尽管,我是那么地惧怕死亡这两个字。我曾多次在深夜的网络里,问不同的熟悉的和陌生的人:“你们怕死吗?死是什么滋味?死后,人会有感觉吗?”然后,我在各种类似“想这个太累!”“精神出问题了?”“你越来越无聊!”等诸多名目繁复的答案中终于消失。——当然,我只是消褪在他人的QQ上,让自己的头像在深夜中从别人的视野中黯淡,带着最初的疑问,独自去继续等待第二天会出现的或阳光或风雨。
——没有经验可循。是的,死去的人无法再传授经验。而活着的人又怎么会知道真实的感觉。一个朋友告诉我,死就和昏倒的感觉一样。不会有痛苦。但是这答案可信吗?毕竟他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一位有过自杀经验的朋友说,当他把煤气罐的软管塞进嘴里时,他感觉自己像飘了起来,好象灵魂出窍,像一个自己看着另外一个自己。这种感觉我信,但是疑问还没有解答。因为他形容的只是死亡前的一种感觉,而他并没有真正死去,也就无法代表那种感觉就是死亡全过程的最终体会。
其实,只要一谈到死,就会有人骂我。或者有人逃离。有关生死的文字总不及有关快乐、笑话,或是性那样令人感兴趣,因为人生在世实在需要更多的乐趣。社会的现实压力还不够大吗?还要故弄玄虚,耸人听闻来搞这么沉重的话题?死,毕竟是可怕的。谁又不想多在世上活一天呢?
但死,到底有多可怕?我第一次见到死人,是一位朋友。她的双手紧紧攥握,帮她穿寿衣时,我发现那原本温润的手变得僵硬而冰凉。那一刻,我看见她微闭的双目仿佛瞑思。我甚至想,她临终时一定有很多渴望未曾表达,而深感遗憾或是倍加对这个世界不舍。而后,当我刻意去听朋友们讲有关死亡的真实故事,以寻找某种相似的体验。无一例外的是,这故事中有同样一个真实的情节,来做为我探寻的答案——死去的人们的确都紧握着双手。这就不得不让我开始怀疑“撒手人寰”这个成语的真实性。
按生存着的体验来分析,人们在紧张,在忧伤,在心绞痛时,都会握紧拳头。而在舒适,坦然,放松的状态下,则会双手敞开。所以,有心理学家主张这样一种修为的方式:当你紧张时,记得静坐,把双手平放身体二侧,掌心面天,自然展开,很快就可变得平静与松弛。据我的观察,这样的方式在瑜伽功中也可以见到。甚至很多保健功中都有把手掌自然放开的动作。
既然如此,我是否可以推测——如果人在死亡时感觉痛苦,她的手便不会张开。这种痛苦未必来源身体,也许是心灵。尘世间有太多放不下,而生命的逝去有太多遗憾与不舍。世界又有实在太多的东西值得留恋。握紧与放开对活着的人来说无可厚非,对死去的人更不值一提。但对一个等待死亡临界的而言,我想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那一刻,如果没恐惧,没有痛苦,没有梦想颠倒究竟,自然进入一个平和的境界,死亡就可以变成一种快乐。一种人生极限也是唯一一次最大的快乐。有了快乐,可以消除不安,烦恼。有了死亡的快乐,人们也就不再害怕死亡,或是说,活着时,可以更加快乐地生龙活虎地享受生活。
是的,把死亡当成一种快乐,听起来是一种极为浪漫的思想。宗教中常常教导人们这样享受人生最后一刻。但在此,我不是为了宣扬宗教的力量,我只希望,在人生最后一刻,我仍然体会到平静、光明、愉悦感与难以遏止的幸福。其实,这也许是很多人的共同的心愿。
因为如今,生命与死亡已经频繁呈现在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中。信息的时代,我们尽可能全方位地接受来自这个地球任何角落里的任何信息。而生命中最初与最终所要面对的生与死问题,也难免要掺杂进世俗。或许,这只是人的自然情感,但不可不承认的是,世界的生活化使生与死越来越失去了神圣礼仪的外衣。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又何需神圣的礼仪?当我们在无知中发出生命的哭泣,通过种种方法,更多地思考了死亡是什么之后,只希望离开的一刻不要痛苦不堪,不要牵肠挂肚,不要忐忑不安,不要所有不好的情绪与肉体体验。坦然地走向未知,舒适地张开双手,拥抱自然。
但是否有能够让死亡快乐的方法?按普通人的心理而言,死亡的距离总是遥远也不愿丈量的。但死亡却因为未知的存在,又无时无刻不再威胁每个人。车祸、疾病、甚至城市中一场骤然而降的暴雨,都有可能夺去一个人的生命。生命之脆弱也使死亡从没有如此地接近每一个人。因此,探讨快乐的尽可能让一种自然仪式变得神圣而庄严,似乎又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对那些经常在研究“人生价值与意义”问题的朋友当中。
前面讲得有些啰嗦。说来,便是我将要做出后面重要结论的前序。虽然比较冗长,却能看到我曾经的思维渐进性。这也许是很多人考虑这个问题时,都要经过的一段路,我们的路不会完全相同,也许会有相似之处。在经过了思考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人的死亡能够为其它活着生命奉献一些价值,死亡对他便不再恐惧痛苦。因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死等于消亡,但尤于他奉献了一种价值,让一个人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他的生命,他的死就晋升为一种神圣的仪式。
“人生百年,终化一捧灰泥,身后诸事将息;青山白骨,若留半息灵魂,生前万般喜乐。”人生哪怕三十年,八十年,亦或一百二十年,那临终一刻,若能以一种神圣的仪式重演生命的开始与继续,那会是多大的乐趣与幸福呢?而在活着时,能为不知何时将要上演的仪式,做一个精心的准备,那会不会也是一种乐趣与幸福呢?


 重症肌无力病友之家 → 文字心情 → 生死谈
重症肌无力病友之家 → 文字心情 → 生死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