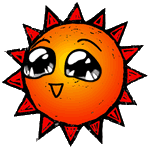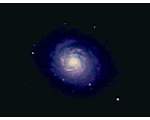重症肌无力研究进展
作者:何国胜
一、发病原因
何国胜等认为遗传因素在挛生子重症肌无力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其对1983年~1999年诊治的2351例MG进行了研究,发现有挛生子11对,占总病例0.45%。其中男8对(72.7%),女3对(27.3%);单卵挛生子9对(81.8%),两挛生子先后发生MG6对,发病一致率66.7%。双卵挛生子2对,其中男1对,女1对,为同性别双卵挛生子,仅有其中之一发病,发病一致率为0。经x2检验,发病一致率二者间差异有显著性(P<0.01)。 发病年龄,所有发病的17例中,发病年龄0~9岁年龄组10例(58.8%),10~19岁年龄组6例(35.3%),20~29岁年龄组1例(5.9%)。在双方都发病的6对单卵挛生子中,最大发病年龄12岁,最小发病年龄1岁。双方发病的同一对挛生子间发病年龄间隔均在3年以内,其中1年内3对,2年内2对,3年1对。临床表现:所有病例均仅单纯眼外肌受累,按改良Ossermann分型,均为1型。乙酰胆碱受体抗体:按常规ELISA法检测,血清乙酰胆碱受体抗体滴度大于0.5mmol/L为阳性。14例检测了乙酰胆碱受体抗体,阳性11例,阳性率为78.6%。双方均发病的6对单卵挛生子均检测了乙酰胆碱受体抗体,5对双方均高于正常,1对一方高于正常,一方阴性。合并症:6对双方患病的单卵挛生子中,4对行纵隔CT或MRI检查,2对同时有胸腺增生或胸腺瘤,一对双方均正常,一对其中一方胸腺增生,另一方正常。6对均未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研究结果提示在MG发病原因中遗传因素起重要作用,但也与环境因素有关。并且遗传因素对20岁以前发病比20岁以后发病所起作用更大,对单纯I型MG发病比其它型更为重要。而Agafonov BV等报道,9对单卵挛生子中有4对双方都患MG,另5对仅其中一方发病,单卵挛生子发病一致率为44.4%。而9对双卵挛生子中仅其中一方发病,发病一致率为0。这种结果上的差别可能与种族差异有关。说明在东方汉族人MG发病中遗传因素所起作用更大。
二、发病机制
自1672年英国Thomas Willis首次描述描述了第一例重症肌无力(MG)之后,Erb 及Goldflam报告本病的突出表现为眼肌和延髓运动神经支配的肌肉无力,症状在一天内有波动,Jolly指出症状在休息后缓解。1934年Dale发现在神经肌肉接头(NMJ)处存在着乙酰胆碱(Ach),1935年Pritchard用吡啶斯的明治疗本病。Viets(1953年)指出在MG患者中有15%伴有胸腺瘤,有65%伴有胸腺增生,有关胸腺与本病的关系受到人们关注。1952年Herrist用皮质类固醇制剂治疗MG。1973年Patrick和Lindstrom用电鳐发电器官中提取的AchR蛋白注射给家兔成功地制成了MG模型,开创了揭示MG发病机制的新纪元。Fambrough等(1973)利用α-银环蛇毒素(α-BuTX)与AchR单一结合的特点,对NMJ超微结构进行观察,Engel(1977)指出MG时突触后膜短缩、简单化。自80年代后期人们清楚地认识到MG时AchRab就是针对靶器官NMJ的突触后膜的特异抗原、即AchR的循环抗体,免疫应答的特异抗原就是AchR,并应用患者或实验动物的血清以及免疫活性细胞制成本病的被动转移或应用AchR主动免疫的模型。明确了MG免疫应答是一系列免疫事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细胞免疫应答可能有着较重要的作用。
1.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中的肿瘤坏死因子(TNFs)、转化生长因子(TGF-β)、干扰素(IFNs)、IL-1、IL-2、IL-4、IL-6、IL-10、IL-12等在重症肌无力发病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TGF-β作为一种重要的内源性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具有抑制Th1及Th2产生IFN-γ、IL-4等的功能。Schluesener发现TGF-β可抑制大鼠星形胶质细胞自身抗原表达并下调IFN-γ或TNF-α产生的MHCⅡ类抗原的表达。Shull发现TGF-β基因去除的动物可产生多个器官的炎症。Ma CG发现,在MG的动物模型,实验性自身免疫性重症肌无力(EAMG)中,免疫耐受鼠淋巴器官中AchR活化的TGF-β mRNA表达细胞数明显增加,提示TGF-β在免疫耐受中起免疫抑制功能。Link等观察重组的TGF-β(rTGF-β)对MG患者PBMNC细胞因子的mRNA表达情况,发现它可抑制AchR诱导的炎性因子TNF-α、TNF-β、IL-6及穿孔素的产生,但对另一种免疫抑制因子IL-10及TGF-β自身没有影响。这些研究显示TGF-β在疾病免疫的负相调节中起重要作用。张栩等应用体外细胞培养和ELISA方法检测MG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经乙酰胆碱受体(AchR)刺激后产生TGF-β的水平,以探讨转化生长因子β在重症肌无力(MG)免疫病理机理中的作用。结果MG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TGF-β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且TGF-β水平与病程有关。AchR特异性TGF-β高于对照组,说明MG患者免疫功能失调,在启动免疫激活机理的同时,也启动了免疫抑制机能。病程>5年较≤1年者TGF-β水平进一步增高,说明随着病情的缓解和稳定,MG患者内源性免疫抑制功能得到增强。结论是TGF-β参与了MG的免疫病理过程。
2.血清阳性MG(SPMG)
特异抗原AchR是分子量为25万的酸性糖蛋白,糖约占30%,带有负电荷,等电点在4.5~4.8间。其分布因肌肉而异,三角肌中约有(4.0~5.7)×107个,肋间肌中约有(0.9~1.9)×109个,平均以10 000/μl个积聚于突触后膜皱折的顶端,半衰期5~9天。AchR是由4条多糖肽链以α、β、γ、δ五聚体形式组成,直径约8nm。与Ach结合的位点在α链上,故每个AchR有2个结合位点。虽然2条α链相同,但对一些拮抗剂的亲和力却不尽相同,免疫的特点也有所不同,AchR抗体通常只能阻断一个α-BUTx结合点。AchR分子穿通突触后膜,约有50%的部分凸出膜外,40%在膜内,10%则深入到肌细胞浆内。循环抗体AchRab是一种多克隆抗体,针对受体决定簇产生几种IgG亚型。AchRab有60%以上直接作用在AchR的α链第67-76氨基酸片段,这些片段因能与多数抗体结合,被称为主要免疫原区(MIR)。AchRab具有亲水性,带负电荷,有较高度的保守抗原特性,其损害NMJ的主要途径有:由补体介导下的破坏;由于F(ab')片段与受体交键,受体内在化率增加,影响AchR代谢;抗体直接封闭AchR与配体的结合位点;AchRab和AchR结合引起受体构象改变而导致受体对配体失敏感。
胸腺在MG发病中有特殊的意义,正常胸腺髓质及周围淋巴组织内的肌样细胞内的AchR在成熟T细胞内,但较增生胸腺内的含量少。在增生的胸腺髓质内其含量较多,与表达主要组织相容复合体(MHC)Ⅱ类分子密切接触的指状细胞(IDC)密切接触,IDC可促进胸腺内T细胞发育成熟,在胸腺内抗原递呈细胞(APC)的参与下发挥细胞免疫作用,其数量与胸腺增生程度呈正相关。胸腺瘤内无AchR,胸腺瘤上皮细胞内α五聚体的mRNA的决定簇则是刺激T细胞的决定簇,但这些T细胞来源尚不清楚。MG患者胸腺内的发生中心有对AchR特异的T细胞,胸腺内如何启动自身免疫应答,可能是(1)APC将AchR呈递给成熟的T细胞,激活了的T细胞演变成对AchR特异的T细胞群;(2)感染源和宿主蛋白间有共同的氨基酸序列,产生了对“自身”决定簇的交叉反应;(3)胸腺瘤内的15.3Kb蛋白既不与α-BUTx结合,也不表达MIR,但与AchR部分交叉反应形成自身免疫原。
约有85%的MG患者血清AchRab阳性,AchRab与NMJ处的AchR结合阻断了AchR离子通道,在补体参与下融解,破坏AchR,引起肌无力;另有约15%的患者血清AchRab阴性,但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用TE671细胞株观察结果表明AchRab阳性的IgG和AchRab阴性的非IgG均对抑制甲酰胆碱诱发的钠内流起主导作用,推测非IgG抑制AchR过程中IgG抗体发挥了主要作用。现已知MG时胸腺内AchR反应性T细胞含量高于患者外周血内的含量,更明显高于正常,患者外周血细胞CD4+亚群中表达CD29记忆T细胞明显增高,可溶性IL-2R水平也增高,这都表示出MG时细胞免疫应答状态。
近来研究表明MG病理改变是NMJ突触后膜短缩、简单化,突触后膜与前膜长度之比变小,神经末端内囊泡空泡化,突触后膜上的AchR减少超过35%,为与其它肌病鉴别提供了病理学检测依据。MG出现锥体束征,除和本病与其它自身免疫疾病如红斑狼疮、多发硬化等合并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害有关外,尚与中枢神经系统内Ach代谢异常有关,还可能与肌无力所致颈椎关节平衡失调造成的颈椎病有关。
3.血清阴性MG(SNMG)
约有10%~15%的MG患者,与SPMG有相似的临床特征,对胸腺切除术、胆碱酯酶治疗、免疫抑制剂和血浆置换术治疗有效;多见于轻症病人,单纯眼肌型较多,胸腺病变较少见,且不患有胸腺瘤;男性病情较轻,女性病情较重。有学者作回顾研究发现有胸腺异常的MG患者中只有6%为血清阴性,而胸腺正常的MG患者有33%为血清阴性,SNMG患者胸腺正常的比例(75%)约为SPMG(28%)的3倍。但在其血清中检测不到AchRab,推测其原因可能为:①标准放免法不能检测特异性的直接针对毒素结合位点的抗体, 因此只具有此类抗体的MG患者表现为血清阴性;②抗体都已与运动终板结合,血清中已无循环抗体;③AchR抗原决定簇的变异可能导致抗体不能与检测抗原反应;④在放免法检测的溶解过程中AchR关键决定簇已丢失;⑤抗体可在体内与终板AchR原位结合,但不能与提取的受体蛋白结合;⑥免疫沉淀法中所用受体来自于截肢人腿肌肉,后者含有大量胚胎型AchR,且用免疫沉淀法检测不到IgM抗体,所以用此法检测结果为阴性的MG患者可能有针对成人型nAchR(包括ε亚单位)的抗体,或只含有IgM抗体。
1986年Mossmann等首先提出,SNMG在免疫学和生理学上有别于SPMG,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实体。其发病是通过抗体和NMJ处AchR以外的决定簇结合而妨碍了神经肌肉传递。依据为:①使用AchR混合制剂的放免法对检测微量AchRab十分敏感,但未能在SNMG患者血清中检测到AchRab;②通过抑制α-BuTx结合试验证明SNMG患者血清中不存在和AchR结合的抗体;③将SNMG患者免疫球蛋白注入小鼠腹腔,可引起神经肌肉传递障碍,但未能发现和小鼠AchR结合的抗体,而在注入SPMG患者血清的对照小鼠中,则发现有74.5%的AchR与IgG型抗体结合。
此后的研究发现,SNMG病人的胸腺髓质有明显的淋巴结型T-细胞区域,生发中心数量较少,在体外培养的胸腺淋巴细胞IgG产量较低,无AchRab产生,与SPMG 病人及正常人均明显不同,这些均提示SNMG发病机制不同于SPMG,是免疫学不同的两个疾病。
Birmanns等随访观察12例SNMG2~30年,发现全身型SNMG病情较重, 对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眼咽喉肌型SNMG有相对温和的病程,对免疫抑制剂治疗效果不好。其中5例患者行胸腺切除术,病理组织检查均正常,且在体外均不分泌AchRab。从而提出SNMG可区分为两组疾病:全身型SNMG是一种不同于SPMG的自身免疫病,眼咽喉肌型SNMG可能是一种非自身免疫疾病。
研究发现,SNMG母亲所生婴儿可有短暂性新生儿MG;被动转移SNMG的血清可致小鼠NMJ处的AchR减少和微小终板电位(MEPP)降低;血浆交换可使临床症状改善。这些都表明SNMG血清中存在致病因子,寻找致病因子已成为研究SNMG发病机制的热点。
研究表明SNMG外周血淋巴细胞及骨髓淋巴细胞中均存在IgG型AchRab分泌细胞,但其数量小于SPMG患者;有人用能表达胚胎nAchR的小鼠肌管及快速应用系统,证实SNMG患者纯化IgG能可逆阻断nAchR离子通道;Burges等所SNMG患者的纯化IgG注入小鼠体内,注射后第15天,发现所有患者的IgG均引起小鼠MEPP波幅降低,且终板电位的乙酰胆碱(Ach)的量子释放量也明显减少,从而提出SNMG是自身抗体介导的自身免疫病,IgG抗体是其致病因子。Verma提出在胸腺正常的SNMG病人血清中存在“神经肌肉阻断分子”,其成分可能是正常胸腺分泌的胸腺因子如胸腺素α-1、促胸腺生成素或白细胞介素。其特点是:阻断传导和破坏AchR能力较弱;②诱导胸腺增生反应能力较弱或无此能力;③对肢体肌肉的亲合性差;此类分子可能有胸腺外来源。
最近的研究发现,SNMG血清中非IgG成分能短暂抑制nAchR功能;用酶联免疫检测法从SNMG患者血清中检测到能与胎牛AchR结合的IgMAb;SNMG患者纯化IgM可抑制nAchR22Na+流。这些研究结果提示在SNMG病人血清中可能存在低亲合性的IgMAchRab。IgM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补体活化剂,而在SNMG患者NMJ处已发现补体成分,推测可能是补体依赖的AchR溶解导致神经肌肉传递障碍。
SNMG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能够对人为在AchR-α亚单位的肌无力源性多有肽(P195-212和P259-271)产生增殖反应,而且SNMG病人抗原提呈细胞(APC)的MHC-Ⅱ类分子能高效率的结合并提呈这二类多肽。这表明SNMG的淋巴细胞至少对NMJ处AchR的某些部分是敏感的,大部分SNMG患者有针对AchR的自身免疫性发病机制。Bufler用单克隆抗体所做的研究发现,与NMJ处Ach结合位点结合可导致nAchR离子通道阻断,而与受体其他抗原决定簇结合则不出现如此结果,但与nAchR结合位点或其附近部位结合的抗体不能被免疫沉淀法检测到,故推测至少部分SNMG患者存在直接针对nAchR-α亚单位结合位点的抗体,可功能性阻断nAchR离子通道。
Yamamoto研究证明SNMG患者血清中致病因子通过与NMJ处AchR以外的成分结合,引起突触后膜损害。已发现的AchRab之外的自身抗体有抗突触前膜抗体、抗横纹肌抗体、抗细胞骨架蛋白抗体等。这些抗体都能与NMJ处AchR之外的结构蛋白结合,破坏AchR而影响神经肌肉传导。
最近有学者用定量免疫斑点技术研究发现SNMG患者IgG和IgM没有针对肌肉抗原的任何反应,表明SNMG患者没有直接针对AchR及其附近靶抗原的自身抗体,且未经治疗的、或已行胸腺切除的及接受免疫抑制剂的SNMG病人的自身反应性抗体成分与正常人没有区别,这表明SNMG患者缺少对肌肉抗原的损害反应是其固有的特征。其研究同时发现,SNMG病人IgG和IgM抗体成分对胸腺抗原有选择性损害,且同SPMG的抗体成分相同,提示血清阴性和血清阳性MG有相同的免疫病理学特征,SNMG自身反应性B细胞的扩增是受B细胞对胸腺自身抗原的特异性限制的,胸腺在SNMG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信使系统在SNMG发病机制中的作用,B2肾上腺素能激动剂、沙丁胺醇、钙调基因相关肽(CGRP)和霍乱毒素等可通过与人类横纹肌肉瘤细胞系TE671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结合而增加细胞内cAMP含量,提示SNMG患者的免疫球蛋白可能通过与细胞表面特异性抗原交联,产生细胞内cAMP和/或其他第二信使,使得AchR磷酸化,从而降低AchR功能;同时NMJ的这些抗体可能在体内通过脱敏作用和/或损害突触后膜,激活补体从而破坏AchR功能[18]。Barrett等用全细胞膜片钳技术研究SNMG患者血浆对TE671细胞AchR功能的影响时,发现其血浆均对电压门控Na+内流无抑制作用,但能迅速而显著的减少Ach诱发的nAchR离子流,他们提出nAchR离子流的减少不可能归于抗体对nAchR的破坏作用,因后者需几个小时时间。同时研究发现部分SNMG血浆对AchR功能的抑制作用是钙离子依赖性的,表明在NMJ处与AchR磷酸化有关的第二信使系统可能参与其发病过程。Ca2+对许多细胞内通路均有调节作用,如参与活化磷脂酶C(PLC),而PLC可催化二磷酸肌醇转化为三磷酸肌醇和二酰基甘油;Ca2+也可调节蛋白激酶C(PKC)的强化。Ca2+的这两种作用导致细胞质和膜蛋白中磷酸化的增加,而nAchR的磷酸化既可抑制其功能,且抗体对淋巴细胞的作用也可能是由PLC和PKC介导的,为IgM的第二信使作用提供了先导,而IgM是SNMG抑制因子中最可能发挥作用的免疫球蛋白亚群。
4.超微结构
宋东林等用电镜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神经肌肉接头处突触后、前膜的超微结构研究进行观察,方法是将肋间内肌在辣根过氧化酶标记的α-银环蛇毒素(HRP-α-BuTx)标记后,用图形扫描及医学图像分析软件测量电镜照片中NMJ的各项指标,并与对照组比较分析。结果5例MG突触后膜长度缩短,后、前膜长度比值变小,神经末端面积及其与突触后膜面积之比变小,突触后膜上的乙酰胆碱受体(AChR)减少了35.9%。结论是MG时NMJ的变化主要存在于突触后膜。突触后、前膜长度之比对本病的诊断更有临床意义。
5.糖皮质激素治疗重症肌无力早期致病情加重的机制
文诗广等研究了36例重症肌无力,男17例,女19例,年龄16~68岁,平均42岁,病程1个月至15年,平均12.6个月。治疗采用甲基泼尼松龙冲击疗法,根据临床绝对和相对评分法评价肌无力的临床症状,采用低频重复电刺激检测神经肌肉传导阻滞程度,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血清中AChRAb的滴度。激素冲击治疗中出现肌无力加重者占55.5%,13.8%累及呼吸肌,5.5%出现肌无力危象。肌无力加重出现于冲击后1~7 d,持续1~18 d。肌无力加重时临床绝对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血清AChRAb滴度,加重前后比较无明显变化(P>0.05)。桡神经、腋神经的低频重复电刺激(RNS)波幅递减幅度较加重前明显增加(P<0.05);副神经的低频RNS波幅递减程度较加重前增大,但无显著性意义。提示其肌无力加重可能与激素对神经-肌肉接头处的传递阻滞作用有关,与Miller等报道的“大剂量激素早期对AChR离子通道有直接阻滞作用”相一致。
三、治疗现状
1.西医治疗
理想的治疗目标是特异性抑制对AChR的免疫反应而不干扰免疫系统功能、无毒而且长期或永久有效。目前提倡不管有无胸腺增生或胸腺瘤尽早行胸腺手术切除为治疗本病的首选方法,但儿童型MG有约30%的可自愈,应待其治疗效果不佳或确为胸腺瘤时,或待其成年时症状仍存在再行手术切除胸腺为宜。胸腺切除后仅部分患者血清AchRab很快下降,症状缓解,多数患者短期内血清AchRab不降低,症状好转不明显,甚至个别患者有所加重。这与体内AchRab逐渐破解有关,一般需经2年,长者需经5~7年症状方能消失,此间仍需服用适量的皮质类固醇制剂和胆碱酯酶抑制剂。1990年Gekht对20例经胸腺切除、胸腺区放疗、激素治疗、血浆交换法治疗无效的MG病员采用脾切除,症状缓解率达65%。
已往采用的皮质类固醇制剂大剂量冲击疗法,由于副作用较大且易出现“反跳现象”,现已为递增疗法取代,即视病情逐渐增加其剂量。
大剂量免疫球蛋白可抑制或干扰AchR与AchRab结合,抑制AchRab合成及产生,增加外周血Ts细胞,干扰补体的激活过程,阻碍AchR破坏,下调自身免疫反应;动物实验表明人AchRab制备的兔抗人独特抗体(Anti-Id)在体外能抑制80%的AchR与AchRab结合,Anti-Id与AchRab亲和力较AchR与AchRab的大3~4倍,制备出临床针对AchR特异性的Anti-Id尚需时间。
用其它免疫抑制剂治疗的研究虽十分活跃,尤其是特异免疫治疗,但尚无定论。如将AChR与蓖麻毒的毒性A链或125I相偶连制成免疫毒素,在体外可特异性杀伤B细胞,清除抗AChR抗体。但其缺陷是:①抗AChR抗体在循环中存在,能结合免疫毒素,形成免疫复合物,沉积于肺、肝或肾脏中,使治疗不能到达目标,而且还会损害这些脏器。②如果有记忆B细胞,能增殖,导致自身免疫反应复发。③即使能完全消除对AChR特异的B细胞,由于B细胞具有抗原诱导的体细胞突变能力,又能产生新的对AChR特异的B细胞。
用基因重组技术制备的IL-2毒素,含有IL-2R结合部位及白喉毒素的细胞毒部分,能够与含有IL-2R的细胞结合,通过细胞内吞作用进入细胞。不可逆的抑制蛋白质合成,导致靶T细胞死亡。在用AChR免疫小鼠时同时给予IL-2毒素,可以使抗AChR抗体的产生减少50%以上,抑制实验性变态反应性MG( EAMG)发生;但对已建立EAMG小鼠的抗AChR抗体水平无影响;而体外试验证实,用IL-2毒素能明显抑制AChR特异T细胞的增殖及抗AChR抗体的产生。体内外试验的不同结果可能来源于在整体动物中IL-2毒素的生物利用度差和半衰期短。
Thompson等用V β6特异的免疫毒素( VIT6)在体外能抑制B6小鼠的 AChR反应T细胞的增殖及抗AChR抗体的产生,选择性杀伤表达V β 6的AChR反应T细胞 。使小鼠多达50%的V β基因失效,小鼠仍能保持正常免疫反应,未发生免疫缺陷,提示V β特异的免疫治疗较非特异免疫抑制剂更安全。VIT治疗MG的关键是确定疾病所使用的特异TCR-V区。目前发现MG和EAMG对AChR反应T细胞使用的TCR有异质性,消除少数TCR仅有一定效果。
用某种抗原活化的T细胞免疫动物能诱导特异性针对该抗原的免疫无反应性,这种方法称为T细胞疫苗,能抑制对异体移植的免疫反应并能抑制几种由效应T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病,如多发性硬化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用AChR 致敏的T细胞处理大鼠能产生轻微的但是确定的针对AChR的免疫无反应性;若再用AChR免疫动物,接种了T细胞的鼠能产生更高水平的抗AChR抗体,但其脾脏细胞在体外产生抗原特异的抑制,因此用抗原特异的T细胞接种可引起阳性的抗体反应和抑制的细胞反应,抑制效应来源于接种的T细胞针对特异抗原的TCR。
用抗CD4抗体消除Th细胞,不仅对EAMG治疗有效,Ahlberg等还对1例57岁的女性患者进行了治疗,给药后肌无力症状迅速缓解、重频刺激递减现象消失、AChR反应T细胞消失、IFN-γ持续增高,抗AChR抗体有所增多 。结果表明,抗CD4抗体治疗使临床和电生理缓解,并非由于消除了抗AChR抗体,提示T细胞直接或通过细胞因子作用参与了神经肌肉接头的传递障碍。
Shenoy等用IFN-α成功地抑制AChR和CFA(complete freund’s adjuvant)诱导的EAMG,改善了肌无力症状、减少了抗AChR抗体产生、降低了淋巴结细胞对AChR的增殖反应、下调了MHC-II类的表达而促进了MHC-I类表达 。
将个体自身的APC作为向导导弹去攻击特异针对AChR的所有T细胞库,B细胞能呈递与其表面Ig结合的抗原,因此可作为APC。体外试验表明,B细胞能将AChR呈递给AChR致敏的大鼠T细胞,刺激其增殖和产生IL-2,但这些T细胞对AChR刺激不能再增殖、产生IL-2及对B细胞起辅助作用,即下调了抗 AChR的免疫反应,而对其它抗原如卵白蛋白能起免疫反应 ,Mclntosh等用偶联了AChR的同基因的脾细胞免疫Lewis大鼠,也能诱导特异针对AChR的免疫耐受。
Souroujon等预先用AChR肽免疫兔,再用AChR和CFA免疫,仅产生短暂的非致死性EAMG;未经AChR肽预处理的对照兔则全部发生致死性EAMG,提示肽的预先免疫能使抗AChR朝向肽所代表的非致病性决定簇,有效地诱导特异性免疫耐受,从而预防EAMG的发生 。
Shenoy等用AChR和CFA免疫具有MHC-IAβ67、70和71位点基因突变的bm 12小鼠对AChR自身免疫反应弱,不发生肌无力;而无突变的B6小鼠能产生EAMG,表明改变MHC-II类分子能抑制EAMG的发生 。
针对MG患者体内存在的AchR特异的CD4+T细胞制做有特异性的TH疫苗、抗CD4+抗体和特异性抑制细胞因子Ts F以及干扰T细胞识别抗原物质如抗MHO-Ⅱ类抗体、多肽抑制剂等也在研究中。
2.中医治疗
研究表明,补中益气汤为最常用的方剂,黄芪是中医治疗MG的要药,因其主要成分黄芪皂甙及补中益气复方制剂,能明显降低肌无力患者周围单个细胞遗传学损伤的作用。若阴虚,宜配伍熟地;阳气不足,宜黄芪配桂枝;元气大虚,宜黄芪配鹿茸;身倦乏力明显,宜黄芪配人参。肌肉萎缩,可配伍牛膝。配合针灸可加强疗效。
(1)辨证论治 孟如主张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病结合起来,立足分型论治:中气不足,常见于单纯眼肌型,治以健脾益气,补中升阳,补中益气汤加味;②脾肾阴虚,常见于全身肌无力型,治以温补为主,四君子汤合六味地黄汤;脾肾阳虚,常见于全身肌无力型,治以温补脾胃,四君子汤合金匮肾气丸;气血亏虚,常见于各型久病者,治以气血双补,十全大补汤加减;脾虚气弱,湿热内蕴型,宜标本同治,投补中益气汤合温胆汤加减;气虚血瘀阻络型,常见于全身肌无力久病后,治以益气养血、活血通络,四君子汤合桃红四物汤。李忠林分为三型:脾胃两虚型用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党参、当归、大枣、巴戟天、补骨脂、黄精、紫河车、鹿角胶。脾肾阳虚型用西洋参、黄芪、白术、附子、肉桂、紫河车、熟地、山药、枸杞子、山茱萸、锁阳、补骨脂、淫羊藿、鹿角胶。脾肾气阴两虚型,用左归丸为主,药用党参、黄芪、生地、熟地、山药、枸杞子、山萸肉、龟板、白术、何首乌、天冬、阿胶。共治42例,结果痊愈24例,有效10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80.9%,李庚和等分为三型:脾胃气虚型,药用黄芪、党参、升麻、柴胡、白术、甘草、当归、葛根等;脾肾气阴两虚型,药用生地、熟地、山茱萸、龟板、枸杞子、制首乌、赤芍、五味子、党参等;脾肾阳虚,药用黄芪、党参、制附子、鹿角胶、熟地、巴戟肉、锁阳、怀山药、甘草等。结果痊愈11例,显效18例,有效20例,无效1例 。
(2)专方 刘作良治疗MG10例,用制马钱子、红参、黄芪、当归、山药,按1:6:6:2:6比例配制,马钱子用量1日不超过0.5g,治疗1个月加服补中益气汤。本方服至症状完全消失后,再继续服用2个月,结果经4~6个月治疗,症状完全 消失者8例,明显好转者2例。付玉如等用起痿方(熟地、菟丝子、鹿角片、淫羊藿、当归、党参、制附片、黄芪、白术、天麻),并随症加减,治疗12例,治愈9例,好转2例,无效1例,李燕娜用强肌宁(含天麻、全蝎等),补肝强肌汤(胆南星、菖蒲、僵蚕、钩藤、黄芪、杜仲炭等),3个月为一疗程,治疗MG129例,治愈71例,显效56例,无效2例,总效率97%。李顺民等用强肌健力胶囊(黄芪、党参、白术、当归、柴胡、五爪龙、甘草等),连续服用1~4个月,共治MG23例,痊愈5例,显效、好转各8例,无效2例,血清乙酰胆碱受体、抗体和抗突触前膜抗体治疗后均有下降。王立华用黄芪、党参、白术、仙灵牌、葛根、鸡血藤、熟地、枸杞子、附子、肉桂、陈皮、甘草治疗本病,也取得显著效果。邓铁涛用强肌健力饮(黄芪、五爪龙、党参、白术、当归、升麻、柴胡、陈皮、甘草),重补脾胃,益气升陷,兼治五脏,治疗MG126例,临床治愈7例,显效93例,好转17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为92.8%[3]。尚尔寿治疗单纯眼肌型或全身型较轻者,只给强肌宁胶囊(含全蝎、蜈蚣、地龙、天麻、杜仲、牛膝、黄芪等),症状重者配合复肌汤,重用黄芪,配补中益气扬,长期用激素或减激素过程中,注意重用补肾药,结果收到显著效果 。
(3)针灸疗法
郑晓兰等用针刺治疗眼肌型重症肌无力24例,主穴取攒竹、阳白、鱼腰,配穴取足三里、三阴交、足三里、手三里、合谷、光明等穴,采用徐疾泻法。结果临床治愈12例,显效19例,好转10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97%。冯起国等取阳白、鱼腰、攒竹、丝竹空(沿皮下斜刺阳白穴后,依次透刺后3穴)、申脉、足三里针刺留针30rnin,脾俞、肾俞、三阴交等灸。每穴三壮,共治疗MG47例,治愈32例,好转11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为91.5%。
陈健文用穴位注射治疗重症肌无力眼肌型58例。取穴脾俞、肾俞、足三里、三阴交。方法为黄芪、柴胡注射液每次各1支,分注两个穴位,15岁以下首选脾俞、肾俞,成人首选足三里、三阴交。若兼有肾虚症状者,可四个穴位交替选用。 结果痊愈23例、显效25例,好转7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94.8% 。
(4)综合疗法
黄再军治疗眼肌型重症肌无力28例,用黄芪桂枝汤加味(黄芪、桂枝、当归、芍药、制川乌、制草乌、大枣、鸡血藤、附子、甘草、生姜)口服,并用生川乌、生草乌、枳实、川芎、姜黄、生大黄、冰片、樟脑、生附片、广丹、香油熬膏,外贴大椎、膻中、神阙、肝俞、肺俞、足三里、合谷、印堂、太阳火针快速刺入,结果痊愈21例,好转7例。齐玲玲分为脾肾虚弱证,以左归饮加减内服,针灸取百会,瞳子髎、肝俞、肾俞、并随症加穴,配合按摩肾区、头顶部等;脾胃虚弱证,以补中益气汤加减内服,针灸廉泉、膻中、中脘、足三里,随症加穴,配合腹部和四肢按摩;肾气亏虚证,以龟鹿二仙膏加减,针灸百会、中脘、气海,随症加穴,配合腹部、背部背俞穴按摩,并在胸腹部和背部的经络循行线上进行火灸疗法等。
3.中西医结合治疗
蒋方健等中西医结合救治10例重症肌无力危象,治疗中及时经鼻导管插管,呼吸机辅助,正压通气,对症处理,用地塞米松10mg/日静滴,感染触发危象用抗生素,首选头孢哌酮、再根据血、痰培养等调整,并用人参、蛤蚧、熟地、沉香、脐带、附子、煅龙骨、煅牡蛎、灸甘草、黑锡丹、猴枣散,或用生脉注射液静滴,意识不清用温开法加苏合香丸研末,胃管注入;凉开加醒脑静注射液静滴,结果抢救成功7例,死亡3例


 重症肌无力病友之家 → 论文汇编 → [转贴]我所见的最完整的论文,特别推荐!(海蓝港湾)
重症肌无力病友之家 → 论文汇编 → [转贴]我所见的最完整的论文,特别推荐!(海蓝港湾)